6月11日下午2点左右,向莉(化名)接到公司打来的电话,告诉她何俊突然死亡了。蹊跷之余,向莉调取了丈夫死亡前一周的工作记录,发现从6月5日至6月11日,何俊竟然累计超时工作长达48个小时。向莉坚信丈夫是“过劳死”。但现有法律法规对于“过劳死”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补偿标准。(6月30日《新法制报》)
近年来,有关“过劳死”的事件频频发生。2011年4月,年仅25岁的普华永道上海办事处员工潘某猝死,而她的微博上,也早就高频次出现加班、身体透支的记录。2014年,金山旗下游戏公司一名25岁员工在上班时间被发现死于北京的办公室,该员工的猝死,给IT从业人员的健康问题敲响了警钟。
“过劳死”顾名思义,是因为工作时间过长,劳动强度过重,心理压力太大,从而出现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。由于积劳成疾,积重难返,往往会突然引发身体潜在的疾病急性恶化,假如救治不及时,将危及生命。其实,“过劳死”不是中国“专利”,国外也同样存在。据媒体报道,日本每年约有1万人因过劳而猝死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统计,在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等国都有“过劳死”记载。
面对“过劳死”频频夺命,该如何保护“过劳”群体?目前,有关如何维护“过劳”群体的合法权益,中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对此作出明确规定,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一是“过劳死”概念缺失。无论是我国劳动保障范畴,还是法律法规、司法援助,以及医学上都没有明确规定“过劳死”的概念。二是“过劳死”缺乏认定标准。由于个人体质不同,劳累过度之后发生的反应和死亡原因也不同,所以难以认定受害方的“过劳”和“死亡”是否存在证据上的直接联系。三是“过劳死”调查取证困难。用工单位掌握用工资料、用工合同、加班记录等证据材料,而受害方要想拿到这些材料,还需要用工方提供。假如用工方不提供,或者故意销毁、隐瞒,这无疑给受害方维权增加了难度。四是“过劳死”缺乏独立的赔偿制度。目前,针对“过劳死”,只能依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中的“因工死亡”,按照工伤认定。
尽管“过劳死”明确起来困难重重,但面对“过劳”群体,法律岂能缺位?这些困难岂能成为绕开立法保障的理由和借口?虽然原因很多,但与“过劳”群体的生命相比,孰轻孰重?对于“过劳死”立法保护具体做法,不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。作为“过劳死”发生率较高的国家,早在1995年,日本修改了《心脑疾病工伤认定标准》(下称《标准》),在对“过劳死”的认定上,提出了“心脑疾病工伤”概念,并将此法规作为认定“过劳死”的法律依据。2001年,又对该《标准》进行修改,对构成“过劳死”的工伤标准做了具体规定。因此,作为全球劳动力输出最多的国家之一,中国在预防“过劳死”、保障“过劳”群体合法权益上很有立法的必要。
“过劳死”虽可怕,但更可怕的是面对“过劳死”却束手无策。笔者认为,只有通过立法来明确对“过劳死”的界定、约束和严厉惩处,才能从根本上依法保护“过劳”群体的生命安全。这既是维护“过劳”群体合法权益的需要,也是依法治国、尊重生命的需要。
(声明: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新浪网立场。)
最全面的江西生活资讯。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就爱江西(微信号:zuinanchang)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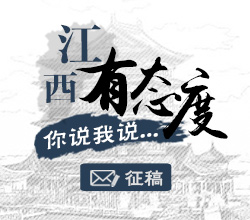
查看评论(0)网友评论
发 表 登录|注册